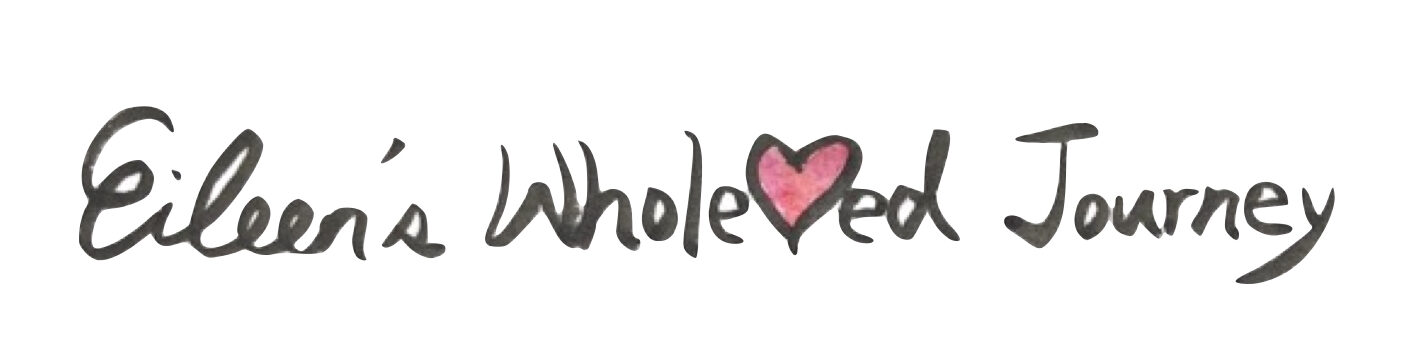生日的幾天前,聽見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消息,曾經跟我在如此靠近的大學生活圈中的生命隕落,在朋友圈中感受到那股無奈的沈重,更無法想像他的家人此刻正經歷的悲痛,這也牽起了我的青春往事,還有那個一直想提筆卻沒有足夠勇氣和力氣來寫的故事,在43歲的生日這天,我想以這個重生的故事,獻給那些早逝的生命以及活過來、或是還正在努力活過來的生命們。
在執著底下的悲痛
在親職的生活裡,我一直對教育有種莫名的熱忱跟執著,在不斷的內心叩問「教育要教什麼」底下,其實是一種對自己成長歷程的悲憤,想知道為什麼自己一路都按著師長講的道路乖乖走,卻是在應該要海闊天空的大學生活裡,不知怎麼掉進了感覺誰都救不了我的黑洞- 憂鬱症,花了許多年的時間跌跌爬爬著走回這個社會所視為正常的道路,花了更多年的是重建自己對自己的信心、重建我的內心世界,這個工程是還在進行中的,已經脫離了那最辛苦的掙扎時期,有足夠的力量褪去社會環境加諸於我但不屬於我的一切,活出屬於我內心的樣貌。在人生的現階段,我很感謝自己能走過曾經的這一段,沒有粉碎就無法重建(every breakdown is a breakthrough),如果沒有這一段,我不會成為今天的我,而我衷心愛著現在的自己。正因為我體會過那個黑洞的可怕,身為一個母親後,這股力量轉換為堅持,一種不想孩子跟我一樣痛苦的堅持,這股堅持也讓我有勇氣去爬梳自己成長的經過,想知道是什麼讓我掉進了黑洞,黑洞到底怎麼形成的,我要怎麼能讓孩子做更好的準備?不可諱言的,這形塑了我在陪伴孩子時的價值觀,我最在乎的是他們內心的土壤,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跟自己相處、面對這個世界的姿態、受挫後的韌性等等,囊括來說就是整體的心理健康。
乖小孩
我從小在親戚朋友叔叔阿姨老師的眼中就是個標準的乖孩子,回家不必催促就會自己做功課,大人說一我不會說二,大概到國小高年級後,就是自己起床、吃完早餐,自己準時6:45出門。從小媽媽就很訓練我獨立,因此小一開始的課後才藝,不管鋼琴、畫畫課,交通都是自己來,走路過平交道、忠孝東路馬路口都不是問題,也可以自己坐半個多小時的公車去學游泳(即使台北市大半的路都不認識),上完再回來,那幾年正逢陸正案件震撼社會,我記得常看見親友老師對於我的獨立(還有媽媽的放手)那種佩服又暗自擔心的眼神。國小唯一一次最大的抗爭,就是在中年級分班時,我很想去申請羽球班,爸媽堅決我要去考音樂班(這個決定在我回過頭來看是很感謝我爸媽的),但這個所謂的抗爭也僅是蹲在浴室門口大哭一場,抗爭力道之小,我媽幾乎不記得有這件事,在我心裡卻是種撕心裂肺的力道。
到了國中以後,更是全然自動化,上學完全不用人叫,六點多依然默默自己出門,我住的是台北市有名的明星學區,一屆考上第一志願高中的平均有一百多個,升學壓力也是出了名,早自習常常7:10就有考試,拿著書邊走邊K到學校是家常便飯,我的功課穩定地進步,到了二年級以後就經常是第一名,媽媽完全不用管我的功課或是擔心聯絡簿上老師的留言,聯絡簿上都是密密麻麻當周小考的成績及全班排名,曾經有幾次我晚上忘了拿聯絡簿出來,早上上學前才急忙拿出來,媽媽躺在床上半夢半醒中就簽掉了,不用操心的程度不言而喻。
平靜下醞釀的風暴
看似不用父母操心的階段,其實在平靜的水面下正是身心劇烈變化的青春期,荷爾蒙的改變引起身體一連串的變化,首先是生理期的種種不便,不能上游泳課等於跟全班宣告你的大姨媽來了,莫名地有種把底褲露出來的丟臉感,常常要擔心量過多的時候,坐太久會不會滲出到裙子的糗事,一邊要專心上課,一邊感受著液體在你腿間流動時的不受控與不安,最折磨身心的,是對於自己身體形象的嫌棄,總是暗暗把自己跟同學們比較(而且都是跟瘦的比),我覺得自己的大腿太粗、小腿蘿蔔太大、沒有腰身、肩膀太寬、臉太大…….我不喜歡自己的樣子,這種對於身體的不安和缺乏自信,更是在游泳課被放大了數倍,男生換泳衣總是比女生快,當女生們穿著泳衣從更衣室魚貫走出來時,要面對的是早就老神在在坐在泳池畔的階梯上等的男生們,從他們前面走過去,如同被用放大鏡品頭論足的感覺,光是想像他們在竊竊私語的內容,我就有種窒息感。
當時的我還有一個習慣,當年不以為意,只覺得自己的行為好笑,當了父母後卻感到種不寒而慄的恐懼。國中的飯後都有午睡時間,就算你不想睡也得趴著,不然被巡邏的糾察隊瞧見,班上的秩序就會被扣分。在那些悶熱的短暫午後,我會在腦海重複開啟夏先生的故事的一個片段,當時的我很喜歡這個德國作家徐四金的小品,這個片段是夏先生在想像如果他過世後,親朋好友來悼念他時會講的種種好話,似乎這個想像可以將他從現實的痛苦中暫時解放出來,這個想像也勾住了我,在那些要把自己敲入半夢遊狀態的午睡時刻,我開始想像自己從樓上跳下去,還有想像種種之後會發生的事,以及我的那些親朋好友們的反應,做完這場人工式的夢遊後,我覺得好像洗掉了些心頭壓力,輕鬆了些。現在回頭想起來,這已經是種求救訊號,對於那種無窮無盡喘不過氣來的生活想要有的解脫,在當時沒有任何的意識或資源的環境之下,我小小的心靈用它僅能抓到的方式在排毒,這件事情我幾乎沒對朋友提起過(更不用說是父母),以前只覺得是自己幼稚愚蠢的行為,不值得一提,當我開始爬梳這一切時,才看懂這是個求助的哭喊,有一次我試著讓神隊友理解在天龍國的明星國中生活是什麼樣子,提到了這件事,頓時從好笑變成了哽咽。
幸好,在這個高度壓抑的環境底下,我還有個關鍵的排毒出口- 運動,在國中時我瘋狂地打球,其中我最愛的就是籃球,我有許多寒暑假泡在球場的回憶,即使是需要唸書的週末,我們有幾個球友- 嚴格來說兩男兩女- 總是會約個瘋狂的四、五點,比賽看誰先到球場,那種帶著球安靜摸黑出門的偷偷摸摸,走在路上有點害怕又有種冒險的刺激感,看見路燈在時間到的那刻瞬間暗去,爬牆翻進學校等待同學來的時光,是種青春期的療癒及成就感,然後盡情地打球打到滿身是汗後,再一起去圖書館K書一一整天,這些跟朋友們揮灑著臭汗、打著嘴砲的時光,似乎讓青春裡激盪複雜無法處理的一切可以暫時安靜一些。
運動跟成績對青春期的我來說,是種安全的需求,我需要肯定自己跟接受自己的浮標。分數跟排名就像是成人世界裡的金錢跟頭銜,左右了那個小小社會裡你的「社經」地位,考高分不但是避免被辱罵或挨打的唯一途徑,更能贏得同學尊敬羨慕的眼光,每次段考大家會照分數排成一條長龍,進來重新分配座位,你的座位就清楚地指名你在老師心中的位置,最中央的兩列是成績最好的,然後依序往兩側窗外排去,最靠窗戶走廊的兩側儼然就是被放棄區。而運動不但是我排毒的出口(雖然當時我並不知道這是排毒),還能滿足我肯定自己的需要。大概是遺傳了媽媽得天獨厚的運動神經,幾乎從跑步、跳遠、各式球類,我都可以駕馭自如,校內比賽也都輕鬆得名,這條運動的線索從國中一路延伸到高中及大學,尤其在神人出沒的北一女,學業不能再成為我肯定自己的穩定來源,我變得更是努力地投身運動場(後來發現從小到大我當最多的班級幹部就是體育股長),成為了滿是甲組球員羽球隊裡的唯一乙組學妹,在這個奇人特多的學校裡,試著尋找自己的價值。
當我回頭看這些年少時驅動我的力量,在這些追求底下,是想要肯定自己、接受自己,更深層的- 其實是對於被愛的需求- 想要可以被尊重、被看見、被珍惜、被好好對待。
講件趣事:在國小的時候,Sanrio甚為風行(大概就是現在的寶可夢或是角落生物?),從Hello Kitty、大眼蛙到kiki lala等等,種類繁多的文具及生活用品皆是價錢不斐,同學間常會比較手上擁有的Sanrio物品,當時的我常常省下媽媽給我吃飯的錢,偷偷去買昂貴的Sanrio文具,然後供奉在我的櫃子裡欣賞,純粹把玩而捨不得用,同學們來家裏時就找他們一起來看,好像看著他們羨慕的眼神,我就可以感到多一點滿足,多得到一點關愛一樣。對於那些束之高閣、捨不得用的Sanrio寶物,在多年後我的感覺自然是不同,逐漸一一分送給晚輩,我試著去理解當時的自己到底為什麼如此瘋狂,想一想,這些文具就像是童年時代的「貨幣」,隱形地影響著你在團體裡的位子,你追求的其實是被同學看見、被接納、被珍惜的感覺- 一種歸屬感,殊不知這樣的方式往往只導致羨慕、嫉妒的情緒,而非真心的連結。
這個貨幣,到了國中之後逐漸轉變為成績及運動,當然也有青春賀爾蒙少不了的曖昧關係,能夠吸引的異性眼光,看起來我追求著不同的目標,底層的需求卻是從未變過。但是最大的盲點在於,我永遠無法滿足這個被愛的需求- 除非我懂得把這個「被」拿掉,懂得先愛自己跟接納自己,才能停止無止境的向外追求,而找到安然於自己的快樂。
我就這麼一路唸了所謂人人稱羨的第一志願,練就了很會考試、很會在競爭的環境中生存、很會溫良恭儉讓跟很能逼自己的本領,另外一個就是偽裝的本事,即使天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也很難發現我的內心如此波濤洶湧,在北一女的那幾年,我一路都留著短髮,不再是國中風頭盡出的狀態,有時甚至是團體中會被遺忘的存在,在這裡見識到的卓越才智天賦以及驚人的努力,成為了我激勵自己的動力,同時在感受謙虛渺小中,試圖尋找自己的位子,聽見自己心裡反抗跟放棄的聲音越來越大,很想來個逆其道而行卻是沒有勇氣,幸好在這裡遇見了相濡以沫的至友,在自己飄搖到邊緣時總是能拉我一把(或是陪我一起瘋癲),青春的鬱悶及千千萬萬的思緒就這麼透過許多的書信紙條,以及不時的補習班翹課時間,稍微有些出口,進入高三時,已經有種欲振乏力的感覺,隨時都會斷片,無法想像自己還要一路撐到聯考,整天拿著媽媽的單眼古董攝影機,埋首於畢聯會的任務,有著公假撐腰,堂堂正正地可以不上課,在教室外溜達拍照,也許是老天眷顧,在擠出最後一絲精力拼學測後,幸運地推甄進入台大。
從一般人的眼光看來,我的生活一路到大學幾乎無可挑剔,我這麼努力,每一個階段社會設定的期待我都達到了,而且家裡環境小康,爸媽願意給我這個獨生女的資源,雖不會溺愛也從不吝嗇,這不應該是通往幸福的康莊大道的開端嗎?
完全不是
大一的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樣,都是報復性地玩,把國高中所有忍耐的部分,想一口氣玩回來,完全沒有學習的動機或熱情,但是好學生的慣性(還有面子)根深蒂固,到考試前還是會大拼特拼讓它pass。當前面壓抑著我的目標都消失了,不再有學校要拚進去,我面對的是這些年壓抑的情緒、思緒以及完全不了解的自己,或者說赤裸裸的人生課題。
尋求被愛的渴望,讓我成為在同學中很活躍的一份子,積極參與班上所有的活動、出遊、運動比賽,深怕自己會錯過任何環節,即使跟同學混了一整天,趕在門禁前回到家,還要繼續掛在BBS上跟同學聊天到半夜,我偷偷慶幸當年還沒有社群軟體。在大學的日子裡,在一段又一段的關係中,試圖填補那個追求,卻總是會感到不同的缺乏,渾然不知那份缺乏是需要往內尋找的,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 我還是單身比較好,對自己對他人都好。我也開始面對不喜歡自己身體的這個功課,沒有制服的日子反而有了新的煩惱,在出門前我會換了又換,怎麼樣都找不到自己覺得夠好看(或夠瘦)的衣服,出門對我越來越難,我的自我批評聲音越來越大聲,曾經在有明確目標時負責督促我的聲音,卻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越來越退縮,每一次要去上課、要去社團、要去球隊練習的難度越來越高,每一次踏出去都需要很大的掙扎,而每一次讓自己失望的經歷又會增加下一次要踏出去的困難。我不知道自己的目標在哪裡?我到底想做什麼?我適合做什麼?我到底是誰?我開始把自己痲痹在不停的電視節目裡,十幾個小時看下去,看到眼睛又酸又痛,因為這樣我就不用去面對現實裡的苦楚跟困惑,但電視關掉之後,我面對的是傾瀉而下的情緒和止不住的眼淚,還有沉到水底撈也撈不到的自我價值感。
有點諷刺的是,我長年練就的偽裝本領,讓我同住屋簷下的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已經掉入了黑洞,我總是可以隱藏所有線索,裝作若無其事,哭也是躲在房間裡,更不用說在學校的同學朋友大概都一無所知,我想,許多當時的朋友可能讀到這篇,才知道當年並肩同行的我正在經歷憂鬱症,這是一種不知道自己怎麼陷入的困惑、深陷其中感到羞恥、還有無法開口求救的痛苦,感覺擁有一切的我沒有資格陷入憂鬱。
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自己正在經歷憂鬱症,是無意間讀到報紙的健康版文章,當中寫到幾個指標,我才開始有了病識感。這個力道之大,粉碎了我一切的信仰和認知,好像把那些年來堆積出來的信心一口氣都吹散,當時的我曾試著短暫求助醫生或是心理諮商,卻覺得沒有幫助而無法持續,我一邊想要重新站穩腳步,一邊又望見再過一兩年要畢業了,急著想探尋自己終極的熱情和目標,以為給自己一個強而有力的目標是脫離低谷的好方法,曾經一度把系上必修都技術性停掉,積極地跑去蹲重考班想去考醫學系,也曾經在教會的緊密的人際網中重新看見了希望,打算做為畢生的志業,總而言之,後面的道路非常漫長而曲折,這不是一篇打算把自己的創傷揭盡的文章,只能說在年輕的歲月中該去闖蕩、冒險、見識的,我都不留餘力地走過了,載浮載沉中我竟也奇蹟般地完成了學業,雖然我常覺得隻身孤獨而行,但其實這當中有很多的貴人撐著我,總是無條件陪我在國父紀念館聊徹夜的青梅竹馬也好,在恆春基督教醫院遇見的醫師也好,教會裡每一個相信我的兄弟姐妹也好,老天爺也好,我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
讓我試圖收尾跟回歸到寫這篇的初衷,這堂自我的課,到我進入親職、職場後都還不斷地在修,只是比起當年需要掙扎著吸到氧氣的狀態,這個階段更有餘裕跟能力可以慢慢修,我常常在親職生活的衝突時刻或是職場的卡關時刻,重新看見以前沒看見的自己,這幾年潛心上了一系列Mindfulness的課之後,我逐漸找到照顧自己及探索自己的工具,我不再那麼怕「自己」,我看清楚那些停不下來的追求或是掐著胸口努力去滿足期待的背後,其實是想要被愛的自己,當我懂得如何真心地擁抱自己、給予自己所需的愛的時候,我的胸口不再緊繃,不再為別人的不悅而不安,不再感到那種我需要變得更好的急迫感,我就是我,yes I can be better tomorrow yet I AM GOOD ENOUGH at this moment。
寫出了是為了..
提起勇氣寫下這篇文章
是希望可以為著沒有辦法開口求助的人發聲,這些文字,也許只描述了身在其中痛苦的九牛一毛
希望更多人可以理解而且不懼怕談論心理健康的議題
精神疾病在我們的社會裡還是個Taboo
人們不會覺得自己有糖尿病羞於見人,但卻對精神疾病羞於啟齒
沒有人想生病
也沒有人沒有生病的權利
我們的心跟我們的身體一樣都有可能會生病
當我們越願意去談論它,把自己囚禁在角落的靈魂才有機會找到出口
這篇文章也為了那些乖巧順從、高敏度的孩子發聲
我一直到最近才察覺自己的確是HSP(Highly Sensitive Person)族群,身為母親,我長年責怪自己在孩子不間斷地哭鬧時感受到的內心爆炸和瘋狂想法,責怪自己跟其他父母比起來耐受力太差,但這其實是我高敏特質的一部分,當我認出自己是HSP時,內心感受到來自接納的舒暢和放鬆。敏感度越高的孩子,越容易感受到周遭的一舉一動及大人的情緒,知道該如何乖順大人才不會生氣,這並不是心機的行為,而是基於想得到疼愛或是安全的人類本能,這在經年累月中也造就成我偽裝的本領。我在讀李雅卿女士的成長戰爭一書中,有一段曾經讓我瞬間潸然淚下,文中她描述遇見一位乖巧的小女孩,但她看見的穿越了乖巧的行為,而是看見女孩內心壓抑的一切而感到心疼,在那一刻,我覺得我被看見了。
我期望孩子不再把乖順視為他們值得被愛的條件,「乖」不再成為所有父母稱讚孩子的唯一詞語,孩子與我們不是同一個生命,有所不同是理所當然,對我來說親職就像園丁,讓孩子在我們面前能展現自己真實的樣貌,我期待一點一滴地發現他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植物!在教導他們社會秩序的同時,讓他們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不是我們期盼的人生。
最後也為了教育場域的期待發聲
考上好的學校 ≠ 人生幸福的保證,更不是通往成功、快樂的必要途徑,對,進入這個溫層會有些社會上競爭的優勢,但人生的喜悅課題遠遠大於此,記得幾個月前在台大校園裡,聽葉丙成分享他在高教現場的觀察,聽到他描述學生們那些絕望的求助時,昔日的回憶讓我的水龍頭大開,無法停下來的窘迫無處可藏,更感慨著二十年過後的教育現場怎麼依然如此,我期待學校裡的教育不再只是著重大腦、灌輸知識,不再讓青年學子有種「什麼都照著期待做得好好,進到大學卻有種突然間被丟到荒野求生」的茫然無措,而是多一點空間可以學習探索自己- 身體也好、情緒也好、內在也好,多一點時間學習怎麼照顧心,著重在如何於脫離校園時,能成為一個獨立且能照顧自己的完整個體,在群體中成為安好的力量。
願我們都能多一些空間探索自己這個神奇、獨特又複雜的生命
找出自己獨一無二的使用手冊
找到適合自己的溫度、水分、陽光及土壤
然後欣賞彼此的盡情綻放
為美好的多元定義而喝采

To Eileen- 親愛的,謝謝你堅強地走過來,我們才能一起看見不平凡的風景~生日快樂!